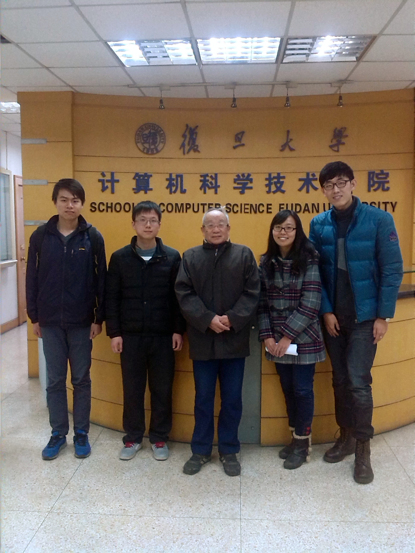被采访人:谢铭培教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荣誉副理事长,国家级专家)
采访人:复旦大学 2013级软件学院研究生党支部 申晨、陈世宜、郑冠仕、
卞景浩
采访时间:2013年12月2日13:00——16:30
采访地点: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逸夫楼六楼会议室
说明:
1. 整个文字版本的整理以尊重音频资料原文为前提,但为了使文本通顺,省略了部分口语化的表达以及对于部分内容做了整理和归纳。
2. 为了使采访文字版稿件的内容更加清晰和条理化,我们在适当的位置插入了一些提问,以方便处理教授口述内容的分段和衔接问题。
3. 若出现文本内容与音频原意不一致的地方,最终以音频原意为准。
4. 原来的采访稿经过教授本人校阅。校阅过程中,除了对个别笔误改正以外,对一些题外话做了大量的删除后,形成这个采访稿。
具 体 采 访 内 容 :
(一)有关的科研业务工作
(二)入党动机与政治信仰
(三)对青年学生的期望和对现实事件的看法
有关的科研业务工作
学生:首先欢迎谢教授能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教授,作为我们学校最早期的计算机研究人员之一,您能简单谈一下当时研究工作的情况吗?
谢教授:我是草根教授,我没有担任过行政方面的职务,也没有做过政治工作。我没有行政干部那样的口才,但是我讲的话都是真实情况和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我们就从早期的计算机谈起。复旦大学第一部计算机不是数字式的,是模拟计算机,是由物理系在 1956 年做出来的。当时我正读高三,在报纸上看到复旦大学试制成功模拟计算机,复旦最早的也是全国最早的模拟计算机,那个时候的型号是 “复旦 601”。
1956 年,我国在苏联帮助下制订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开始时苏联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是后来苏联不再帮助中国,中国产生了科技危机。到了 1958 年大跃进,当时大跃进的思想也比较严重,许多很浮夸、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想要做出来。媒体在炒作要大家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经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达到的目标,而我们现在就要跑步进去,那怎么行啊!
由于大跃进的原因,工农业遭到严重破坏,赶美超英的口号日益盛行,大家都在那里大炼钢铁,我也参加土法炼钢,当时我还做过炉长,其实炼出来的都是一些废铁。
不过我觉得大跃进对科研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什么叫科研?科研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你想搞什么尖端的东西,就可以搞。科研不一定要马上出成果,关键是培养人才。在 1958 年,我们学校研究原子能、计算机、火箭等方面的人很多,科研条件比较艰苦,大家都是凑到一起研究,想要成功,就要拼命苦干,所以说,大跃进对科研的影响远小于工农业,当时的科研是在培养人的。
当时全国都在搞计算机,而上海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三个学校的数学系抽出一部分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在复旦大学组织了一个计算数学训练班,大概 150 人。除了计算数学训练班,还有其他训练班,比如原子能训练班等。
计算数学训练班再分三个班级:程序设计班,计算机机器(现在称为硬件)班,计算方法班。当时我在机器班,最艰苦的就是这个班,其他两个班级都有课上,我们没有。因为计算机原理谁也不懂。由于当时学习资料奇缺,我们就将苏联的一本快速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说明书作为学习教材。每人分配一章自己学习,理解后讲给大家听,每人既是学生也是老师,就以这样的方式学习计算机知识。大概过了一年左右,计算数学训练班就被分开,大部分人分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少量的人留在复旦。我当时留在复旦。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原来在复旦物理系参加第一代计算机(即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的研究工作(后来他们发展壮大了就独立出去了)。我们机器班就调到物理系一起搞计算机硬件。我们一面工作一面自学电子学知识。当时我们样样干,焊接、木匠、钣金都要做。研究组只有 10 个学生和 1 个助教。后来两个学生被调到上海科技大学(就是现在上海工业大学的嘉定校区),后来从北京大学数学系分配来一位教师,一共 10 个人。大家按照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进行分工,我主要负责存储器的研究。由于是电子管计算机,所以当时需要的电源功率很大。我用的最高电压是 500V,我也做电源。材料自己买,电源变压器也要自己加工,不过,交流电机、250 伏直流电机和 60 匹功率的制冷空调机是买的。
经过大家的努力,1964 年初,样机出来了。位数是定点 32 位,速度是每秒 3000 次,存储量才 1KB。要实用就要扩大存储量。那时的存储器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当时最先进的存储器是根据美籍华裔王安的博士论文提出的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磁性材料做的磁芯存储器。磁芯是个空心圆柱形,外径 0.8 毫米,内径 0.6 毫米,高度 0.5 毫米,一个磁芯存一个二进制位信息。这种磁芯当时还买不到。我们就与上海无线电十一厂磁性材料车间(后改为磁性材料厂)联合试制。因为我是搞存储器的,就派我去。这项工作属于粉末冶金,与计算机知识毫无关系。但我们科研组的传统是 “只要工作需要,不管是事务性工作还是技术性工作都不计较”。这试制工作要将多种氧化物和稀土元素配方好再球磨、用金属模具压制后再烧结而成。这些工作包括开模具,我都要做。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终于成功了。当时 1964 年做出 16KB 的存储量,机器可以正常运行实际应用了(型号是复旦 602)。当时自己设计制造电子管数字计算机成功的单位只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在是国防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时给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培养人,编程序的人,计算方法那一类人。有个老师,书看了以后来算,误差多少、按照什么公式去算,结果他有时发现怪事了,怎么老是收敛不起来。他就再查书发现,苏联一本教科书上面莫名其妙一个公式中不做任何说明加了一项。奇怪,把它加进去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否则一直出不来。因为这个误差迭代,差一点你就迭代不出来了,计算机不是无限高的精度,算的是互相逼近迭代出来的。所以实际上训练了一大批人,效果就是这样。 研究生也在上面做了许多科研工作。
学生: 谢老师,你后来还做了哪些科研工作?
谢教授:文化大革命其实只影响我一年左右的科研工作。我们与上海第二机床厂联合研制数控车床。我们负责数字控制装置。该数控车床多次到国外参加工业展览会。该项目获得 1977 年上海科技进步奖。数控装置在复旦大学校办工厂生产了 12 台,产值 150 万。1985 年为上海第三钢铁厂搞过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该项目涉及局部网络、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处理和自动编程,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为中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学生: 谢老师,你还编写过计算机教材吗?
谢教授:1971 年编写过《晶体管数字计算机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以 “复旦大学四•一综合仪器厂” 名誉出版的。
学生:那您出书能拿到稿费吗?
谢教授:没有稿费。我只拿到两本样书。后来又编写了一本《智能模拟》(就是人工智能),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入党动机与政治信仰
学生:我知道您是一名老党员,党龄一定很长。您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您当年入党时的动机?
谢教授:党龄长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重要的是,随着党龄的增长,自己的政治信仰是否更纯洁更坚定。
我 1957 年申请入党。当时我的动机是两个:感恩和光荣感。
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感恩思想。我出生在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年 (农历是 1937 年 12 月,阳历 1938 年 1 月份)。日本人没有到我们那边去过。但是我见到第一个日本人是飞行员。那个飞机飞得很低,我们几个小孩很怕,觉得飞机要撞到学校的屋顶似的。当时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看到了飞行员。我当时唱的歌都是抗日歌曲,例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日本的侵略,生活很苦。1943 年至 1944 年,一年当中,死了三个人(爷爷、父亲和弟弟)。我有两个姓,我姓谢还有姓蒋。因为我妈妈怕有我哥哥和我两个男丁要被国民党抓一个去当兵。我妈妈就把我与舅父同姓(我舅父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我小学毕业后,辍学了一年半。解放后有了助学金,我才开始读中学。所以我读书动力非常足。你想想看,有书读还不读好么?(画外音:很珍惜这样的求学机会)。(笑答)就是。不然我就没有出路了是不是?因此我很感激共产党。
第二个,共产党实在是伟大。刚解放时我辍学在家里,一批批解放军部队住过我村,向老百姓借水桶、借扁担、借工具。他们的话老百姓听不懂,其实他们山东话我也是半懂半不懂,但勉强过得去。我当解放军的翻译。我跟解放军很熟。他们的生活很艰苦。一天只吃两顿饭。七月份大热天生病的时候,没有药物,就在晒谷子的石庭上铺上棉被,上面再盖上三床棉被, 在烈日暴晒下,人还冷得一直在发抖。偶尔领到大蒜,是战士们最开心的时刻。星期天休息时还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门口,修道路。共产党伟大,入了党当然也光荣。1959 年我入了党。
共产党员不能因为感恩入党,要有共产主义信念。入党后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在写转正报告时,我彻底把它想通了。
学生:能谈谈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吗?
谢教授:佛教,教人要做好事,他修的是来生投胎投得好一点。所以佛教是修炼来生的。基督教是修炼死后上天堂的,是修炼死后的事。这两者都与现实生活脱离的。虽然道教是修炼这一生的。但他们三者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修炼个体的。共产主义不一样,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且是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要把天堂在人类现实社会中建成。当然需要几十代人才能够实现。我是享受不到的,但要为共产主义这个理想而奋斗。想通以后我把转正报告交了,这个政治信仰我从没有变过(哪怕苏联解体时也没有动摇过)。在 1966 年我结婚的时候,我按我的名字(铭培)和我爱人的名字(唯群),自己写了一副对联:“铭记一生党栽培,唯念终身为 ‘愚’ 群”(这个 ‘愚’ 是 ‘愚公移山’ 的 ‘愚’,不是 ‘愚蠢’ 的 ‘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对青年学生的期望和对现实事件的看法
学生:嗯,非常感谢,谢谢谢教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您之前的一些早期经历,包括科研当中的很多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有启发性,也对我们未来无论是在科研方面或者是在党性这方面的认识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真的非常谢谢您。您能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党员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吗?或者说对我们提些什么期望?
谢教授:根据我的体会,我建议你们:在业务工作上要尽量扩大知识面并且认真负责做好自己该做的工作;在政治思想上要爱国。
校训的 “博学而笃志” 很重要。计算机应用面很广,几乎所有学科都可用到。因此要尽量扩大知识面。我接触到的除了计算机本身的硬件、局部网络、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处理、自动编程、模式识别等等以外,还有电子学、机械、炼钢、粉末冶金、机床、化工、拉单晶、中医。当然不是盲目扩大知识面,而是有机会就不要放过要抓紧学。管理学院的初期是管理学系,开始时教师比较少。管理学系主任要我帮忙指导三个学生做毕业论文。在指导过程中我还向他们请教管理学方面的知识。我就是这样不耻下问学来的。
要认真负责做好每件事,不会是轻轻松松的,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在搞车床数控装置时,在调试的时候,连续运行四小时就出一个故障(多出了一个脉冲)。重新启动是好的、不连续运行也是好的。想要混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你来验收好了,你没耐心看四小时。领导来看,没问题,走了。我骗他们是很容易骗的,但是我骗不了自己。为了查这个故障,从后面的电路一级一级往前查。每前进一级就要四小时。即使找到原因把它改好了,也要再花八小时考验两次。为此在工厂里连续干了三天两夜。只躺在长凳上休息一会,还不一定全睡熟。就是睡熟了,总共也只有三十分钟。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不可能脱离政治。有的人喜欢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中国的一套格格不入。现在很开放,他可以到国外定居,我也赞成。我在 1989 年 8 月到美国一年。就听到有人在议论:“有个人到美国后经常不管什么事就乱骂中国政府怎么怎么不好。后来他出麻烦了,受欺负受冤枉,惹法院官司了,赶快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就出面,帮他解决掉,没事了!出事时他倒没有骂中国政府,可是事情解决后过不了两天,又破口大骂中国政府。” 我没有听过他骂,但其他人就在议论,说 “这种人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你原来骂就算了,政府帮你解决了这个事情后,你就少骂两句不可以吗!没有什么大事就臭骂一通干嘛呢!” 人家当时不反驳他,背后会议论的。如果你们出国去,千万不要做这种人。但如果要在中国生活,就必须爱中国。如果不爱国,做香蕉人(黄皮白心),就会很痛苦。中国取得的点滴进步,别人做的是中国梦,他做的全是噩梦。所以一定要爱国。爱中国就不要与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党员更要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呢?现在有别的政党可以出来领导中国?有吗?没有!有的说国民党可以。我认为不可以:国民党连一个小小的民进党都摆不平,能领导全中国吗?你不能先把共产党翻掉了再说。像利比亚?好吗?利比亚那个时候,首都得黎波里还没攻下来的时候,就死了两万人。它的人口有六百万,我们中国有十三亿,按这个比例算下来,中国相当于要死掉四百三十多万。难民还不算。你忍心吗?所以爱国就要中国稳定。
要从内心里热爱中国,就要搞清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生命力。
学生:谢教授您对社会主义制度怎么看?
谢教授:。其实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苏联解体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资本主义革命在欧洲也有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到底社会主义有没有生命力?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和古巴几十年,不但古巴没有垮,中国反而和平崛起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反过来,如果美国被封锁五十年,哪怕是三年,后果恐怕是无法设想的。只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好好搞,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
学生:现在网络在人们的日常沟通交流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谢老师觉得应该如何看待网络上的一些言论?
谢教授:网络是放大镜也是显微镜。偏僻小山村的一件小事在网络上一发布,一夜间全国都知道,变成大事。现在网络上包括社会上把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抹黑当成一种 “时尚”。骂共产党虚伪、骗人、是强盗,是土匪。这些骂法。一点创意都没有。我从小就听过,听了六十多年。共产党不怕骂的。中国共产党的特点你们知道吗?骂是骂不倒的,什么时候会倒?捧。吹捧,党就倒了。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是绝对权威,人家吹捧他,就犯大错误了。
对网络上和社会上(即使是好友)的一些传言,你们没有亲自验证过的事,绝对不要轻信或盲从乱传播。我举个例子,我出国去的时候,跟我一道搞项目的一个青年教师,他比我晚半年去,去了以后他给我打长途电话,他问我:“谢老师,你受学校处分了?” 我说:“你比我晚半年出来,如果我受处分了你应该知道的,你还要问我啊?” 他说:“是啊我也在想啊,那个时候没有嘛。是不是你出国了以后再处分?” 我说:“我在美国才处分我。不是叫我别回国还是到那里逃难去吧。这可能吗?” 我问他从哪里听来的,他说是加拿大。国际谣言居然弄到我头上来。所以,听到所有的谣传,我都是抵制的。
学生:你对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怎么看?
谢教授:对于美国的那套宣传必须冷静分析。如果跟着美国走,那就糟糕了。美国一直要中国民主选举。我们要向谁学啊?西方有女皇、天皇。那么我们中国也来搞一个皇帝?倒是台湾真正民主选举啦,直接选。美国也是二级选举。你美国为什么不向台湾学。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都是选举出来的,不听你的话就叫独裁,把他干掉。沙特是皇室独裁;美国应该最恨的,为什么不干掉?再说人权问题。美国的人道主义轰炸够虚伪的。
我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很好了。但中国的人均 GDP 很低,城市化很低,要像台湾那样选举,是不可行的。要这样子搞选举,我敢保证,选出来的是贩毒集团,他们最有钱,什么都敢干,你不投他的票,他一枪就把你干掉。台湾那样的选举,也不是好榜样,一年到头都是乱哄哄的。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就完蛋了,四分五裂,比秦始皇的时代还惨。
我觉得我们不要像 “愤青” 那样跟着美国乱愤。例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抓了七十个。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相当于中国抓了三百个。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别说抓了三百个,就是只抓了七十个,美国会对我们怎么攻击?
学生:你对现在的腐败怎么看?
谢教授: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早在 1980 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大家工资低经济困难,都想法以各种名目多分点钱物。当时有句流行语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当时我讲了一句笑话 “现在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所以,社会有腐败的土壤。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土壤更加肥沃。现在是积重难返。现在习近平大力反贪,有些成效。但两三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希望习近平在十年的任职内能好好解决问题。
我觉得现在对贪官的惩罚不够严。我认为讲不清楚来历的赃款和脏物应该是两个罪(受贿罪和行贿罪)并罚,不能只罚受贿罪。因为这个赃款和脏物的发生就包含了:人家行贿你的行贿罪和你的受贿罪。现在你隐瞒了别人的行贿罪。到时候你监牢里出来了,因为你没有揭发他,人家总要给你点报答。可见法律有漏洞。我也不赞成像愤青那样要把贪官都杀掉。杀掉了,新的线索就没有了,还未揭发出来的贪官最高兴。
学生:谢谢老师,您给我们讲了很多很有用很真实的东西。再次衷心感谢您!
2013 年 12 月 2 日
谢铭培教授接受访谈后与学生合影